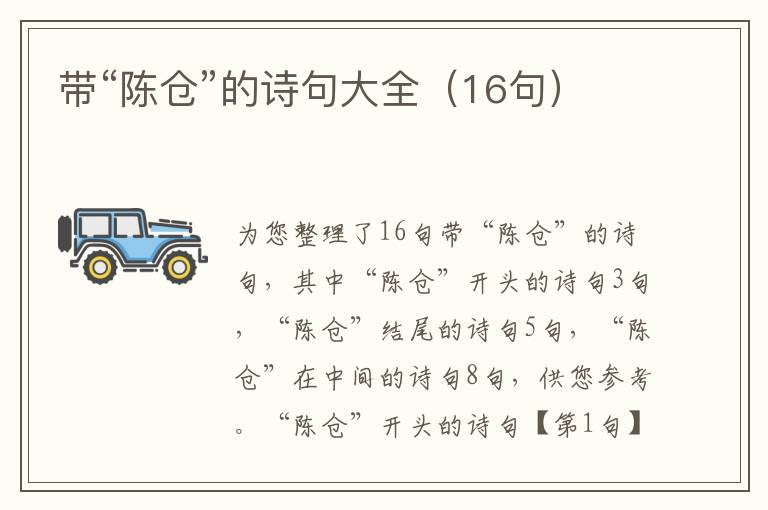隔世守候,靜聆海是誰的淚

busy living,busy loving;never end,never hurt。 ――序
【PART 1】
有點意猶未盡的味道了。
果然已是立春,春天來得立竿見影。夏顏是被窗外沙沙的細雨聲吵醒的。說是吵醒,倒不如說是吵下床。如此沉寂的深夜,除了這溫柔的雨聲,陪伴她失眠的只有空氣。
手機屏幕上亮熒熒地顯示著兩點四十分,依舊失眠,她索性趿著脫鞋拉開了紗簾。窗外夜色濃郁,彌漫著濕漉漉的霧氣,高高矮矮的小樓房鱗次櫛比,一條條弄堂便在沒有形狀的斜風細雨中深深淺淺地一路延伸。上海的郊區,縱然沒有外灘的流光溢彩和花團錦簇,卻總在不經意間隱隱流淌著古典的韻味。
毫無疑問她依戀這個城市。這里灑滿她和她深愛的人生活過的痕跡,每一寸空間都是曾經脈脈溫情的浪漫,每一分空氣都有他離開后楚楚思念的凄婉。六年了,像今夜絹一般的雨絲,她早已戀上這座城市。她愛他,不訴離殤。“你在時,你是一切;你不在時,一切是你。”不知哪里看到的句子,卻聽得讓人心頭滲出水來。
他叫許定安。夏顏收到他的最后一份禮物是一袋細細軟軟的沙子,卡通信紙上他凌亂地寫著:“這是印尼蘇門答臘島一種很神奇的沙子。你在海水中踩上它,便會有如泣如訴的哭聲響起,可是它離開水后又馬上恢復正常。所以,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――哭砂。”除了她,沒有人知道他為什么會千里迢迢送來一袋沙。
他無限熱愛攝影,大海和夏顏是他作品中永遠的主角。從19歲清湯掛面的她第一次遇到他,到22歲他最后一次和她吻別,三年色彩斑斕的青春,像是一道風景,有著透明的底色叫浪漫。
雕欄猶在,朱顏未改;韶華已逝,歸航不返。
閑來無事的時候,他總會帶著她從外灘坐上好長時間游輪去蘆潮港黃埔江的入海口玩,看潮來潮去,聽濤聲依舊。海、天、江融為湛藍的一片,美得像古希臘的神話。她蜷在他懷里,聽著他的心跳應著海潮的節拍――咚咚…咚咚…她不是很好的女孩子,敏感、乖戾、倦怠,倔強的眼睛帶著華麗的蒼涼,不知刺傷多少殷情的目光。定安說,他就是愛上她眼神中清澈空靈后的堅強,靜靜暗涌、緩緩流淌。他總說她是沙,敏感得讓人驚詫,執著得讓人心疼,總有一天會在他海一般浩瀚的愛情滋潤下溫和起來,總有一天他會融入她的一片汪洋中。
于是他真的去了,他說他去印尼拍一些海景,一去不返,留下一袋沙、一座城和她六年的空白。她抱著那袋沙周游四處,只要有海的地方都有她的腳印。她整日喃喃自語,身體像是一陣煙,沒有形狀,也不出聲響。有時候她甚至在問自己:“六年,我到底在堅持什么?六年,我到底在尋找什么?”…是誰說過:“當堅守已經沒有意義,徒勞的又豈只是愛本身?”。
“算了,是時候再出去走走了。”她嘆了口氣,撥通了何天宇的電話。生活中,有這么一個人,能隨時隨地愿意聽自己說話,還是蠻幸福的。“有些話,有些時候,對有些人,你想一想,就不想說了。找到一個你想跟他說,能跟他說的人,不容易。”想起演員王志文在《藝術人生》的采訪中曾如是說,夏顏不禁莞爾。
【PART 2】
加完班已是晚上九點多,年終財務總結,免不了要起早貪黑、披星戴月。何天宇走出公司大門,疲倦讓他沒有一點兒食欲。
公司離家并不是很遠,兩公里的路程,他已經習慣每天步行著回去。歲末將至,本來就熱鬧非凡的大街又鬧騰了許多,目之所及都洋溢著喜慶的紅色,鞭炮聲、嬉鬧聲、吆喝聲交織成一片,超市的大功率音響喜氣洋洋地在唱著:“金風送喜來,迎春花已開…”
路邊,一個賣花的啞巴小姑娘對他打著手語:“哥哥,新年好。”
何天宇討厭這樣的夜晚。這個國際化的大都市,無論何時總能在歌舞升平的繁華中滲透出絲絲徹骨的世態炎涼。車水馬龍、人聲鼎沸,霓虹燈不停地閃爍,印著某當紅女星迷人微笑的巨型廣告牌飛快地變幻著顏色,像這個城市今年很流行的“閃戀閃婚”,轉瞬即逝,飄渺虛無,廉價而光艷。
當然,除了夏顏。
何天宇經常會回想起第一次和夏顏相遇的情形。大約是他剛來上海的時候吧,大學剛畢業的小伙子年輕力盛,還沒對公司上下龐大復雜的人事關系網輕車熟路,處處受挫,傍晚下班后煩悶之余便跑來看海。于是,他遇見了夏顏,這個讓他牽掛一生的女子。
她安安靜靜地站在海邊,白衣飄飄,裙裾紛飛,被海風吹亂的長發在落日的余暉中跳躍著迷離的光點。海溫柔地呼吸著,“嘩-嘩-”,細碎的浪花輕輕撫摸著她的腳踝,沙灘上有青色的小蟹爬來爬去,夕陽西下,漁歌唱晚,像一幅金色的油畫,干凈得沒有一點雜質。
“嗨,裙子濺濕了!”
“那就濕吧!”她沒有回頭,淡淡的聲音像冰冷的海水滲過他的皮膚。
“不早了,要漲潮了,回去吧!海邊風大,會感冒的。”
……
“你說,海是誰的淚?”她微微顫抖了一下,突然扭過頭問道。
“嘸?這個…不知道…”他猝不及防:“可能…是魚的吧!”
“不對,海是沙的淚。”她搖搖頭說:“無論在哪里,只要有海,就能聽見沙哭的聲音。”
“哦,知道了。”
她沉默了,他也沉默了。不同的是,她是沉浸在對往事無限的懷念中,而他,則是沉醉于她漆黑的眼眸中,像兩汪深邃悠久的潭水,冰涼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卻又緊緊揪住他的心,陷進去、再陷進去――凜冽的親和。
天宇搖搖頭,加快了步伐。不遠處,一個馬路歌手在輕聲吟唱:“誰畫出這天地又畫下我和你,讓我們的世界絢麗多彩;誰讓我們哭泣又給我們驚喜,讓我們就這樣相愛相遇;總是要說再見相聚又分離,總是走在漫長的路上……”
許巍的歌,寂寞而不孤單,滄桑而不凄涼。
【PART 3】
五年來他一直在追問夏顏,那天為什么突然會問起那個問題,她總是含笑不語,或者微側著腦袋說:“你去問沙呀!海邊好多沙呢!沙知道答案。”謎一般的女子,總是讓他束手無策,卻又欲罷不能。或許,從那個金色的傍晚,他已經注定要不遺余力地愛上這個叫夏顏的女孩。
傻瓜也看得出他愛她,但不是占有。他知道她不愛他,他也知道她在等一個叫許定安的人回來。他包容她的一切。她神經質,敏感多疑、喜怒無常;她怕陽光,怕尖銳的物體,怕見陌生人,怕空曠的廣場和高地;她明明知道他喜歡她,卻從不留他一點愛的暗示;她夜夜失眠,經常會打電話給他,只是靜靜聽著沙沙的雜音卻一言不發;她說她只是想讓他在電話那端陪她,因為她害怕孤單,但她又從來不讓他靠近。
夏顏的心就像虛掩的大門,他可以推開一條縫兒欣賞院里的風景,卻終究跨不過那道門坎。何天宇知道,那里只允許住一個人,他叫許定安。
他有時也會自嘲,笑自己在愛情面前完全失去理智,笑自己夜夜為她不關機,卻比不上她手中那口袋中的一粒沙。但是沒辦法,戀愛就像放風箏,有的人把線系在手上,有的人卻系在心上。比如他,比如夏顏。夏顏是他的風箏,紙折的翅膀,心無所依、四處漂泊。風箏是注定要在天上飛的,他拽不到懷里,卻也不忍放手。
滬上初雨,靜聆清月。他輾轉反側,想著公司的事,想著商店的春聯,想著夏顏,想著路邊賣花小姑娘的手語“新年好”,想著后天就是除夕……心里像被窗外的雨飄過,又濕又亂。手機屏突然亮了。
“夏顏,有事嗎?”
“天宇,我想去敦煌。”
“什么時候?為什么呀?”
“定安以前經常說想去敦煌,有海的地方都已經踏遍了我的足跡。我想帶上沙去敦煌看看,越快越好。”
“哦,正好我也休假,一起去吧!”
“那明早再具體商量路線。OK?”
“好。再見。”
沒有人知道,何天宇最想說的,其實是一句“晚安”,Wan an ――我愛你,愛你。
【PART 4】
兩人踏上甘肅的土地時是第二日傍晚,飛機緩緩地降落在蘭州機場,剛出艙門便是凜冽的寒風。大西北獨有的寒冷和干燥無情地迎接著兩位從海邊遠道而來的客人。由于火車春運緊張,天宇不得不聯系了一輛去敦煌的長途汽車。
暮色四合,一路向北,河西走廊的廣袤無垠盡收眼底。大漠孤煙直,長河落日圓。舉目四望全是沙的海洋,近處是沙,遠處是沙,沙的遠處還是沙。
車上大部分是返鄉過年的農民工,四處濃厚的西北口音掩飾不住他們歸家的喜悅。車廂前的小VCD機正放著馮小剛的《非誠勿擾》,舒淇和葛優在北海道的日式酒吧里一邊喝著悶酒一邊對著臺詞:
“你為什么能容忍你的女朋友心里有別人?你喜歡我什么?”
“我就是看上了你的傻,對感情不用說三心二意了,連逢場作戲都不會。他這一頁你還沒有翻過,一旦翻到新的這一頁,你照樣會一心一意。”
……
天宇低下了頭,胸口酸酸地難受。一陣風刮過,沙子鉆進車窗吹進眼睛,生生的疼。抬頭卻看見夏顏定定地盯著自己:“何天宇,你想哭就哭吧!我欠你一場委屈的發泄。”
“我知道你心里難受,因為要照顧一個抑郁癥患者并不容易。”他愣了,手足無措,卻看見夏顏冷靜地出奇:“何天宇,你知道五年前我在海邊為什么和你搭話嗎?”
“大約,我看起來像好人吧!”
“許定安的一去不返幾乎擊垮了我所有的理智。當時我已經三個月沒有開口了,所有的人都說我瘋了,愛上了一袋沙和一片海。那天你讓我趕緊回家,因為海邊風大。你知道嗎?定安每次在催我回家時也是這樣子說。恍惚間我以為他回來了,我甚至有抱著你失聲痛苦的沖動。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他,我知道你也很愛我,我知道我欠你很多。”
天宇苦笑著搖搖頭,他又何嘗不自知呢?他愛她,他以一個男人能給予一位女士最高尚的愛來愛著她。但愛不是占有,而是甜蜜的付出和苦澀的等待。就像窗外呼嘯的寒風,總有一天會把沙灘的積水風干。也許,明天面朝大海時,就是春暖花開了吧!他想哭,卻哭不出來。
旁邊有人好奇地湊了過來:“這小伙兒,眼圈都紅了,不就回家過年么高興成這樣?”
【PART 5】
一路顛簸,昏昏欲睡,到達敦煌已是第二日清晨。農歷大年三十的大街異常冷清,兩人找了個住宿的地方叫“月泉賓館”,很好聽的名字,據說是距離著名的莫高窟和月牙泉不遠。剛放下行李,夏顏就迫不及待地拉著天宇出城去了沙漠。
晨曦初露,朝陽下的戈壁沙波浩淼。長風獵獵,遠處有小小的沙丘在風力的推動下緩緩移動,漫天飛舞的沙子一浪又一浪,打在臉上隱隱作痛。蒼茫的天,寥落的地,無邊無際的沙,不知哪里有“叮當”作響的駝鈴聲傳來。這,便是一千五百年前的絲綢之路了。兩人驚異良久。
“天宇,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沙。”夏顏笑著說:“你看,原來沙在風中也可以像海一樣美。”
“是啊!只見過海邊濕漉漉的沙子,沒想到大沙漠這么壯觀呢!”從小生長在南方的何天宇第一次來西北,也且放下了愁思,滿臉驚奇,手中的數碼相機閃個不停。
夏顏鋪了塊塑料布坐在地上,抱著那袋哭砂,靜靜地對著來往的駝隊發呆。兩人出門時帶了零食和水,在沙漠邊折騰一天沒問題。
去了趟月牙泉,又走馬觀花逛了一圈佛寺,日落時天宇才拎著一大堆紀念品大汗淋漓地趕回來,夏顏還在那里發呆。“看!這是佛珠,剛才開過光的,主持大師說只剩一串啦!可以保平安咯!送給你啦!”他不由分說塞給夏顏一串佛珠,渾圓的顆粒,散發著不諳塵世的檀香。
這個男人,任何時候終究是只想著她啊!夏顏嘆了口氣,眼睛被風沙刮了一天,干澀得難受。
“天宇,我想把哭砂留在敦煌。”
“啊?為什么?這不是定安送給你的嗎?”
“不為什么,只是覺得沙就應該回到自己本來的地方,這樣,它才能活得輕松一些。”
“他叫許定安,26歲。死于2004年12月26日,印尼海嘯。六年來我都是在自欺欺人,我天天等他回來,其實我等的,不過是一個永遠不會應允的承諾。我時常在想,定安為什么會送一袋哭砂給我,也許他是想告訴我,只要我受了委屈,他聽到哭聲就會立刻來到我身邊。他一直希望我每天都開心,生前是這樣,死后也肯定是這樣。”
“定安時常會談起想來敦煌看沙漠,大概是冥冥之中吧!他帶我來到這里,告訴我世界上除了海洋還有沙海,沙不只可以在海水中流淚,也可以在風中笑著飛舞。定安,他想讓我幸福。”
她揚了揚手中的佛珠,如釋重負的樣子:“今天我在沙漠里想了好多。有時候,生活就像這串佛珠,每一顆珠子就是一個坎,但是你必須微笑著把它數完。所以我要把哭砂留在這里,沙,應該自由自在開開心心地在風中飛舞;海,也許只是深埋心中渺遠的記憶了。”
“哧――”,口袋撕裂的聲音,細細的哭砂緩緩傾瀉下來,迅速融入沙漠,又迅速被風刮起拍打在臉上。只是沒有了海水的浸泡,它們已經不會哭了。茫茫沙海,只有呼嘯的風聲和叮當的駝鈴聲。
夜幕降臨,小鎮那邊傳來斷斷續續的鞭炮聲,有人家開始吃年夜飯了,紅色的燈籠星星點點地亮起。幾個過路的本地人在駝背上一邊對他倆招手一邊大聲喊著:“嗨,姑娘小伙子,回鎮上過年啦!”
“是呀!明天就是虎年啦!”夏顏的臉已在夜色中看不清了,但是可以肯定她在笑:“沙漠晚上風大,小心感冒。天宇,回去吧!”
“好,回去吧!”何天宇長長吁了口氣,感覺心如止水,又有些百感交集。突然想起那個賣花的啞巴小姑娘,他拉住夏顏,一邊做手語一邊說:“夏顏,新年好!”
“錯了啦!是‘新春好’,因為是農歷春節。明天,就是真正的春天了呢!”
淚,在那一刻洶涌而出。是啊!明天,就是春天了呢!
遠處,一朵煙花驀地在天邊綻放,清凌凌照亮了半個夜空。